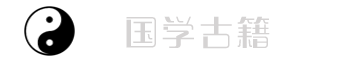《南巫》:当代巫师的离恨乡愁
想想看今年似乎没有进过电影院,也一直没功夫完整地看完一部电影。
直至中秋前后,在营销号的忽悠之下,才看了一部马来西亚的小众电影《南巫》。
本来按照营销号的推荐,说这是一部巫师大战降头师的东南亚民俗恐怖片,可我在屏幕前仔细看了一个多小时:抛去其中出现的不到五分钟的有鬼镜头,剩下的影片其实讲述的是漫长的马来西亚琐碎生活。
但在整部影片结束后,我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。
这不是一部恐怖片,而是一部记载当代“巫师”离恨乡愁的悲哀画卷。
#1
《南巫》的故事非常简单:身为渔夫的男主人公在邻里争端中被人下降头诅咒,不仅开始呕吐出铁钉,身体更开始日渐羸弱,直至濒死。而他的妻子在求助于现代医学无果后,先后求助了马来西亚本地巫师,拿督公,田伯爷,却仍然没能解决问题,最终在退休驱邪师和当地山神娘娘的帮助下,将丈夫从降头术中拯救出来。
与其他精彩激斗的鬼神电影不同,这部电影对于巫术的描写真实得近乎平淡,虽然电影中也出现了降头鬼、山神娘娘之类的超自然角色,但电影更多着眼的是一个平凡家庭在对于“降头”这种怪病诅咒时努力求医问道的挣扎,所以与其说它是一部鬼神恐怖片,不如说是一部马来西亚的生活故事片。
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,在被误解,质疑,批判一百次之后,仍然会在遇到第一百零一次他人求助时,从阴影中站出来。
而原因,只因为他们背负着“巫”这个字。
#2
“巫”这个字,说来简单,却也并不简单。
但是在“通达天地”与“横跨生死”之间,“巫”这个字本身也被“天地”“生死”拉扯的四分五裂。他们虽然能通达天地,却难以真正地融入人类的社会。他们虽然能横跨生死,可是死人的幽冥界他们去不了,活人的人间界他们也过不好。
在如今社会,虽然除了边缘山区以外,似乎已再难见到“巫”的踪迹,但如果从广义上说,东方的风水师,命理师,西方的塔罗师,星盘师;甚至在家的道士,通灵的出马仙,都可以纳入“巫”的范畴。
“巫”这个字看起来奇幻,似乎有通阴阳,明生死,知未来,转乾坤的能力。但一旦背负上这个字,就意味着人生路上自此有着一条与主流社会彻底难以翻越的鸿沟:人们渴望得到巫所代表的神秘的力量,又害怕那冥冥力量后所代表的未知反噬。逐渐地,这种“敬而远之”,就形成了一张无形壁障。
就像《南巫》电影里讲述的那样: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,不会有人谈起与巫有关的话题;而一旦中了降头,那邻居议论纷纷,医生退避三舍。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巫师与鬼神的存在,只是在在生活顺遂时,“巫”是一个让所有人刻意忽视的话题;而在生活遇到波澜时,“巫”是一个让外人避之不及的符号。
因为“巫”所代表的的神秘知识,是与科学所架构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。
于是,这样礼貌的隔阂,把巫与现代社会彻底分隔开,也让身为“巫师”的我们,与主流的生活永恒相隔。
我们站在此岸,望着彼岸,却又两头都到不了岸。
#3
但即便是两头都到不了岸,“巫”却像是一种责任和诅咒,在冥冥中与身为“巫师”的人互相盘桓。
故事始于饱尝丧子之痛的母亲因为仇恨请到了降头师出手,终结于本已退隐的老驱邪师将降头鬼放逐入大海。在这一组链条上的每个人,都不是为了世俗的名与利而出手,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因果在推着他们前进。仿佛一日曾为巫师,就被烙上了这样的终身烙印,注定巫师的一生,就只能在天与地,人与鬼之间挣扎徘徊。
而一旦有了这种印记之后,之后所有的命运和归途似乎就已经注定。
于是,我又想起了我的传承,术士一脉,祖师爷郭璞亡于为王敦谋反之事占卜,六爻的发明人京房因占卜干政死于腰斩弃市,先师杨公殁于为叛王择地…一代又一代的巫,似乎早已经在历史和命运中洞彻自己的结局,却在无情的因果面前毫无迟疑地走上了这条路。
身为巫者,永远与熙攘的现世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;永远与光明的未来有着背道而驰的抉择;永远与静好的人生有着失之交臂的遗憾。
我们用己身,将天地、人鬼、过去和未来统统弥合。最终却注定被更强大的命运洪流撕扯的四分五裂
这就是我从《南巫》中看到的,一份属于巫师自身的离恨乡愁。
在文章的结束,我并不推荐你去看这部电影。
于我而言,《南巫》作为一部小众电影,讲的是马来西亚普通人家的驱魔经历,也讲的是海外华裔难以融入现世的艰难现状,更是讲巫师这个特殊群体在现代背景下的无奈边缘化。
电影里有很多线索,但不同线索的唯一共同点,就是所有人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自己与现实社会的隔膜。
就像影片结尾,坐在小舟飘荡于大海之上,噙着泪花瞭望中原方向的山神娘娘说的那句话一样。
“我,永远都过不了这个边界,永远都回不了我的家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