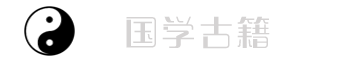麦场
摊了一场麦子,白哗哗的,像白哗哗的汗水汇成的一片麦海,大半年来的辛苦似乎都隔在这儿了。
李家巷里最性焦性躁的兆泰老汉正在扯着嗓子满场吼着:
嫑歇了,嫑歇了,起场了,起场了,没时候了,没时候了……
他每句话几乎都要重复两遍,以示重示,也是强调。但凡涉及干农活的事儿没一样不是他不看重的,他好像天生就是为农活而生的,干瘦、黝黑的脸上只有两撇八字胡须是白的,像场子上臃麦用的榆木推板向两边叉开的两条腿。兆泰老汉的勤劳、性急、暴躁是村里有了名的,总是永不停歇,总是一副狠铁不钢的样子,也总是有干不完的活。队里新嫁过来的年轻媳妇都怕跟他干活,这哪是干活啊,简直是在拼命。兆泰老汉的最后时刻,也是殁在给地里担粪的路上。
现在,离他挑最后一趟粪还有几年的时间,他毫无察觉,依旧奔忙不止。在我们这个村东的生产队里他几乎就是“场”长,那是他的主场,凡进了“场”的人除过队长都要受他管,被他吹胡子瞪眼时时催促,被他一阵急似一阵的吼声淹没,像打仗似的。我们这些小孩子是不会让进“场”的,只能偷偷溜进或是在外面观看,远远地听他打雷似的吼声,看见牛马拉着碌碡在摊开的麦秆上一圈一圈碾着,干热的气息和麦草、麦粒的味道在“场”上弥漫开来,又冲出“场”外,激荡口鼻。这是麦村一年一度收麦的尾声,人们的疲劳大约也到了最后的极限。不过,闻到新麦的香味,再忙再累也是值得的。
南方山区农村的平地叫坪,他们新割的湿稻谷直接在稻田里就可以借打稻机脱粒,北方农村的麦子则要拉回一个叫“场”的平地来仔细晒碾,才能将他们一点儿都不舍得舍弃的麦草、麦衣、麦粒分离出来。若说北方农村最大最平整的一块公共空间,应该就是这用作碾麦的场子了。从我居住的李家巷画一公里半径的圆,大约有三块这样的场子,后来分别由李家、张家、杨家的大部分人共同使用。这样平整的场地,见证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崎岖,曾经与麦共生的跌宕。
集体生产时期,每个生产队都至少拥有一块打麦场,简称麦场,吾乡晋西南人直接称之为“场”。印象里的“场”,始终是一处极豁亮开阔的平地,如古时演兵的校场或阅兵的沙场。场的宽敞、平整,是经过精心维护了的,名曰硌场。水滋润过的场土酥软,可塑性强,洒些碎麦秸和麦衣,牵来老牛,套上石磙,一遍一遍压场,直至出落得一个平整光滑的场,就是硌场。我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,大都先在场上斜跨熟了,才敢大胆腿搭车梁骑上大路,那场地平得跌倒都不觉疼。年青小伙子打赌角力摔跤,一般也选择在“场”,这儿空间大嘛,摆得开,再说若是力气实在使不完,还可以就地搬起几百斤重的石碌碡走一䠀。碌碡,这玩艺原本是农村碾麦用的,过去能搬起的人大有人在,现在的人怕是挪也挪不动了,也不知人的力气都哪里去了。
麦场之大,大在空间和胸怀。
每年麦收时节,这里都吞吐着全队的麦子——麦穗和麦秸,以麦个子的形式簇拥而来,也是麦子全须全尾最后庄严的形式。很快,他们就在这儿被分成了麦秸、麦粒和麦衣。全村男女老幼,都围着麦子转,也牵牛驾车在各自的麦场碾着麦子转。最后,麦粒晾晒在麦场,最好品质的成为公粮,一粒秕麦都没有,留给自己的成为口粮,需要精打细算才够吃一年。麦秸垛子被一杈一杈累积在场子四周,像一个个蘑菇状的硕大的堡垒,晋西南人习惯称之为稴积(音jian ji)。我知道当年那些偷qing的男女也会把这儿当成他们的私秘会所,在顶着几根从稴积窝里粘身的秸秆爬出麦垛前,没少干地动山摇的好事,像《白鹿原》上黑娃和小娥被麦香迷醉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野he。一个巷子里的胜强比我们要大,心思缜密,手脚利落,曾在麦垛子下拣了枚鸡蛋,白花花的令人羡慕,不知谁家的傻鸡憋不住漏蛋,把这儿当自家鸡窝了。后来,我时时注意稴积里的漏蛋,却从来一无所获。
场,全称碾麦场,为麦而生,专场专用,围绕着麦场的许多劳作也深深烙上了“场”的印记。除了前述的“硌场”“起场”“碾场”外,还有“摊场”“翻场”“扬场”“扇场”“扫场”“赶场”“搅场”,主场在“场”,主角是麦,道具有碌碡、磙子、扇车、木杈、木锨等,所有能干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场上为麦而忙。这是最后的时刻,一年辛苦收获的最后时候,也是麦子兑现回报的时候,大家无疑都是忙而开心的,也是我见证过的最忙碌而热闹的晋西南农村劳动场景。许多过来人怀念生产队的那些事情,其中就有那时集体劳动大家可以穷开心,干活不耽误说笑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大姑娘小媳妇,干起活来就渐渐松了正形,打情骂俏算个啥,着急一帮老媳妇敢把老汉小伙子裤子当场脱了让你裸奔。后来,散社分场,一个大场被几家一小块一小块“瓜分”,几家人伙着干才能撑起各自的“场”子来,集体的味道依然还有,那种忙而娱悦的气氛始终在“场”。有时候,赶场误了饭点,当家的一时兴起会买点心慰劳大家,麦子就摊在眼前,收获总算有了保证,人们也比先前变得慷慨。后巷的老姑夫曾开玩笑说这点心吃的,点心纸攒得都可以熰(音 ōu 意“烧”)炕了。
最近看到一段麻雀啄食青麦的视频,始觉一年麦收时节又至。有人在视频评论区留言,说这鸟当年列入四害,看来也不冤它。其实,作为重要产麦区的晋西南,麦子似乎并不怕鸟雀祸害,好像从来没见过谁在麦田里立着假人吓鸟,谷子地就有,鸟雀成群成群的赶也赶不走。麦子成熟后最怕的还是天气突变,或为雨,或为雹,或为风,风旋后的麦地麦子倒伏严重,几乎像被碾过一样,刈割起来也极其困难。南风解愠,风大却委实添忧,“怎么大风越吹,我心越荡”?风啊,最好去做被麦子定义的风。每年麦地里因风倒伏的麦子都是我妈承包慢慢去割,整个人大概需要坐或蹲在地里才能支撑起这样的细致而繁重的劳作。刈割不及时,麦子还会因干燥脱粒减产,或者因贴地湿热而发芽,那种局面真是令人绝望而悲伤。你无法逃脱的宿命里,一定藏着什么命定的不舍的东西,同时还有它们能带给你的全部悲欣与考验吧。
最怕的还是下雨,因此收麦的另一个形象的称号为“龙口夺食”。从行云布雨的龙嘴里抢收麦子,足见雨水对收麦的干扰极大。我妈总说,什么时候麦子都回场了,就放心了。在妈心里,“场”算是麦子一处安稳的怀抱,像我们晚上疯回来躺在自家炕上,仿佛诸神归位。其实,回“场”的麦子,并不见得就是绝对安全的,也怕水火无情来打搅。农民的苦处就在于已经看得见的收获,也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,转瞬之际横遭变故的事儿多了。某年夏收,我们家的麦子刚刚碾毕进屋,大雨就追着屁股来了。侥幸躲过的人,正在庆幸有惊无险,看见邻家的麦子正摊了整“场”要被雨淋,心里不免又沉重起来。虽然已经包产到户“单干”了,但人心竟也没有散尽,大家急火火地一起上手才把他家子救了回来,不然雨一浇,因雨再歇几天,麦苗都能长出来了。据说,真的浇了雨的麦子,在淫雨纷纷的连阴日子里,也只好马不停蹄赶快铺在炕上烘烤了。我没有见识过,但夏日雨天烧炕焙麦该是多么魔幻而辛酸的一个场景呵。
进入九十年代,麦场仍然维持了一阵子,随着联合收割机等刈麦方式的彻底改变,麦场终于失去了用场。当年队里最大的一块的麦场,最终像切豆腐一样被划拨给各个添丁之家做了宅基地,消失得不留一点痕迹。许多年走过来的麦场从此失势,几无踪影,连农村生活标配的麦垛子——稴积,也淡出视线。只有那些刈过的麦子,扬过的麦子,碾过的麦子,晒过的麦子,扇车底下被父亲满意地装进麻袋的麦子,喂进磨面机麦兜里的麦子,一粒一粒装进粮站巨大粮仓的麦子,像远去的金色的时光,仍然在记忆里闪着不息的微光。恍惑间,我亦如当年赤脚走过麦场,成群的麦粒铺垫如毯舔舐得脚底发痒,手握麦穗的孩子,脸上洇着汗水,被日光晒出通红的脸庞。
公众号:竹杖芒鞋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