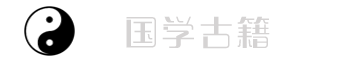鼎罐焢饭香得很
说明:当过知青的人,可能都用过鼎罐。鼎罐历史悠久,用途广泛,焢饭特别香,不知有多少人吃过?还有多少人记得?
鼎罐与古代三足圆鼎的形状几乎完全相同,实际上就是鼎。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肉食和盛贮肉类的器具,有方鼎、圆鼎之分,方鼎又有长方鼎、正方鼎之别。最早的鼎都是用黏土烧制的陶鼎,后来才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。那时的铜好珍贵,铜鼎也就不再用来当炊具了。传说夏禹收九牧之金(铜)铸九鼎于荆山之下,以象征九州,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,让人们警惕,防止被其伤害,是为禹铸九鼎。于是鼎就成为传国重器,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。国灭则鼎迁。夏朝灭,商朝兴,九鼎迁于商都亳京;商朝灭,周朝兴,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。历商至周,把定都或建立新王朝称为定鼎。鼎字也被赋予诸如显赫、尊贵、盛大等引申意义,例如一言九鼎、大名鼎鼎、鼎盛时期、鼎力相助之类。
铜鼎上浮,成为礼器。陶鼎不灭,继续充任炊具。陶鼎易碎,后来可以生产铁了,铁的产量多了,价格降了,于是有了铁鼎。铁鼎用生铁铸造,也可以当礼器,不过大多用在寺庙之类地方。寺庙那插香烛的地方,往往就是铁鼎,大多为长方鼎,且不论。有了铁鼎,陶鼎逐渐被淘汰,作为炊具的铁鼎就是鼎罐。
鼎罐底呈锥形,鼓腹,口圆,上置小盖,两侧有耳。开始时有三足,可以放在地上或灶上,罐下烧火。后来去足,在耳上穿铁丝以为提手,将其挂在墙上或屋梁上,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移动,罐下烧火也就更方便。还有人把鼎罐吊在柴灶的灶门口,借用柴灶飘出的火焰煮食。烟熏火燎,鼎罐通体黝黑。当年,南方农村,特别是山区,包括苗、彝、侗、壮等少数民族,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鼎罐,用以烧水、煮食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我去的是忠县。我们那儿,鼎罐是农民生活的必须品。再穷的人家,即使只有一口破铁锅,甚至没有铁锅,也要有鼎罐。没有鼎罐,不能煮食,吃什么?
在一些地方,鼎罐也叫鼎锅。锅出现较晚,锅直径较大,锅底坦平,但不便移动,只有金属能制,是铁大量使用后才有的炊具。鼎只能煮,锅可煮可蒸可炒,更方便更实用也就更普及。把鼎罐叫做鼎锅,或许是为排除鼎罐原来作为盛具的“罐”的功能,更加强调其煮食功能。事实上,很早很早之前就没有人再将其当盛具了。其实,由于其底部为圆锥,鼎作为盛具并不好用。
我所在的生产队在望水余家岩下。望水原来是乡(公社)所在地,撤乡并村后,如今连个村都不是了,但因保存着一条老街,因而有了名声。那地方海拔虽然只有几百米,但位于迎风坡上,冬天很冷,因而要“向火”。向火就是围着火塘烤火。火塘大多设在堂屋的墙边,火塘上都要吊一个鼎罐。向火时,食也煮好了,就围着鼎罐吃饭。一是暖和,二是节约燃料,三是一家人吃得热闹,三全齐美了。鼎罐用生铁铸造,罐壁往往较厚,很难烧穿锅底,也就特别耐用。农民家的鼎罐大多要用两三代人,甚至用上百年之久。
鼎罐有大小之分。我一个人,生产队给我准备的是最小的,称为三号。我不向火,把鼎罐放在厨房。厨房是正房的偏偏(偏房),矮小,房顶伸手可及,鼎罐就靠着墙吊在屋梁上。对我来说,鼎罐最大的功用是焢红苕。我们那地方穷,生产队一年只分几十百来斤谷子(一斤谷子可以打七两米),红苕却有一千多斤,加上自留地的,多达一吨。每年从国庆节前后开始,一直要吃到第二年栽秧时节。不是当菜吃,是“当顿”!要“当顿”,就只能焢起吃。红苕洗干净,放在鼎罐里,加一点水,鼎罐下面烧火。火不需要烧得过久,然后将鼎罐放在就那“火石”(余火)上,慢慢“捂”。焢出来的红苕水份减少,更甜更好吃。如果火候掌握得好,锅底还会有锅巴,还会有糖流出,虽然可能有一点糊味,吃起却糯滋滋的。如果火烧得过大过久,或者加的水太少,红苕全部或大部都糊了,便只好报废重来。不过,我还没有报废过。
我那时正年轻力壮,肚皮大,吃得多,一顿要吃五斤红苕(折合一斤米)才够。我曾经找来一杆秤,称秤下锅。五斤红苕要装一鼎罐。如果红苕大,例如一斤左右一个的,如果不砍小,鼎罐就装不下。如果红苕小,摇了摇地装,往往还不止五斤。后来,我就以装满一鼎罐为准,只要不装满,哪怕只少了一点点,心理上也接受不了。所谓够吃,只是指把肚皮塞满而已。红苕的有效成份不高,肚皮又没有油水,不管吃得好胀,打几个屁,屙一堆屎,肚皮就空了,又感觉饿。红苕含纤维素多,有滑肠之效,吃了屎多。有时候还没吃完就要屙,屙了肚皮又空荡荡的,还必须再吃。即使不打屁不屙屎,红苕也不“经饿”,上坡挖不了几锄头,那热能就消耗殆尽,身上就没了力气。
红苕吃起来很“哽”人,焢红苕时就在上面放几个萝卜。我们那儿冷,萝卜长不大,只有大拇指粗细,最大的也大不过酒杯口。红苕吃腻烦了,就将焢得软软的萝卜在盐水里醮一下,改个口。我那个鼎罐里,不知焢过多少红苕,多少萝卜。当了两年零八个月知青,最后一年离开时,自由地的红苕已经挖来吃光了,生产队的还没正式开挖。算起来,至少也焢过三四千斤!
如今上网搜,有诸如鼎罐饭、鼎罐菜之类的介绍。鼎罐是生铁所制,盖子又“清丝严缝”,用来炖汤烧肉,味道就别有不同。且不论。我只说我那个鼎罐的故事。那一年春荒,后山一个同学将谷子背到我们前山来打米。往返几十里山路,亏他想得出来。自己用檑子檑,然后用碾子碾,或者用兑窝冲,也费不了这样多的力。打米返回,路过我家,肚皮也饿了。他们生产队分的谷子多,他也知道我的窘况,很大方地打出两大碗米来,就用我的鼎罐煮饭。后山海拔更高,水田的温度更低,称为冷浸田,谷子生长季节更长,米也就更香更好吃。正好我头年从农民手上买了一只羊来杀,还留有一只羊腿。我将那已经风干的羊腿切成小块,放在鼎罐里和米一起煮,只加了一点盐。没想到,那鼎罐虽然盖得好好的,不到半个时辰,竟然也香气四溢。我急忙熄火,让“火石”慢慢“捂”,让米饭慢慢“闷”。那香气让我们开始流口水,他急于要打开盖子看,被我拦住。我说:“要焢出一点锅巴来更好吃。”终于我也忍不住了,打开盖子,香气扑鼻。我把饭瓢伸进去舀了一碗出来。这鼎罐饭火候正好,焢得恰到好处,锅底有一层金黄金黄的锅巴。尝一口,那羊腿肉还硬扎,在嘴里咬着很是舒服,很是有味,久久不愿吞下。那饭粘粘的,糯糯的,香气从口腔钻进鼻腔,然后又直往脑海里冲击。那锅巴一点也没有糊,在嘴里嚼着,嚓嚓嚓的响。虽然没有菜,连咸菜也没有一碟,我们两个饿痨鬼依然把那大半鼎罐饭几乎全部吃光。两大碗米哟,少说也有四斤啊!或许要补充一句,冷浸田的米不“涨饭”,一斤米煮不了两碗饭。我好像只吃了四碗,他比我要吃得少一点。锅底一冷了,那剩下的锅巴就舀不出来。我只好加了一些水进去,再放了一些红苕,熬成稀饭,成了我的晚餐。虽然加了红苕,那稀饭依然酽浓浓的,依然冒着那冷浸米和那羊肉的香气,安逸!
那是我此生印象中最香的米饭。
鼎罐煮饭的确好吃,后来我也煮过。但毕竟没有几颗米,每次煮时我都加了红苕,味道当然不能与羊肉米饭相比。我也在鼎罐里焢过糯米饭,那也好吃,但只焢过一回。生产队只分有十来斤糯米,我要拿回重庆,供家里过年推汤圆用。不过,正因为那鼎罐,焢闷锅饭就成为我的一手“绝活”,如今都还经常焢糯米饭来显示,来得意一下——不过只能用铁锅焢,不可能用鼎罐了。那个鼎罐在我离开农村前一两个月被人偷了,好可惜哟!如果保留到现在,说不定还会成为“文物”。虽然不能与那些出土的高大上的铜鼎相比,但也可以见证我们这一代人的“青春无悔”。
作者:李正权 公众号:重庆乱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