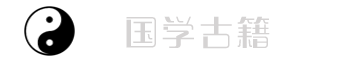一个文人在末世
前几天,《上海书评》上刊登了王培军教授的文章,《读<苍虬阁诗稿七种>》。主要谈的是清末民初诗人陈曾寿此前未被发现的诗稿内容,以及当时诗坛诸位大神对陈曾寿诗作的评价。文章很长,但止于诗与评,未谈其人。
王老师是上古版《苍虬阁诗集》的校点者之一。我闲来偶翻的,就是王老师的这个版本。后来,湖北教育也出版了同名诗集,收录得似乎更全面。
读古诗,能看出它体兼唐宋,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,要求过高,近乎奢求。我们所求者,不过是感受文字,进而能感觉出一点点意境,已然很好。民初诗坛很多大家夸赞陈曾寿的诗,比如散原老人说其诗“沉哀入骨,而出于深微澹远,遂成孤诣。”郑孝胥则说“哀乐过人,加以刻意。”陈宝琛题其诗集有云“九京遗恨君能说,等闲花木有遗哀。”在汪辟疆的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里,陈曾寿位列“八骠骑先锋使”之首,是“天英星小李广华荣”……可见前贤对陈曾寿的诗作评价之高。
陈曾寿,生于1878年,湖北蕲水人,字仁先,号比较多,耐寂、复志等等,因家藏元吴镇画作《苍虬图》,极爱之,以之名阁,后号苍虬居士。
陈曾寿有家学,其曾祖陈沆,嘉庆二十四年的状元,后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。其诗“常有忧勤惕厉之思”。其祖父陈廷经,道光二十四年进士,做过内阁侍读学士。他爹陈恩浦在科场失意,赐举人出身,有个虚衔,叫中书科中书。这个虚衔其实也可以有低微的实职,但据说陈恩浦未出仕。
祖上杰出,陈曾寿在学业和仕途上也没丢脸,他在1903年中进士,从刑部主事,后调学部,后为广东道监察御史,但仍在京中任职。此时,武昌城头一声枪响,民国来了,陈家慌乱,先是举家回乡,但乡间土匪蜂起,一夕数惊。这时候在京城的陈曾寿也匆忙赶回来,商量后决定全家去上海避难。一大家,有四十余口人,按照其女婿周君实回忆,居留上海期间,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到此时,不过是一个传统仕宦家庭恰逢变乱,及其后的正常举止,无甚可观处。可一说的是,在上海期间,一群文人总想着复bi,前后奔走,一直到1917年张勋的辫子军,大伙儿以为大势已成,纷纷出来亮相。在十来天的闹剧中,陈曾寿获授学部右侍郎。张勋的逆时而动很快失败,陈曾寿只得南归。次年,侍奉母亲,在西湖边建房,并作久住计划。
远在西湖的曾经的朝廷才俊陈曾寿是个朋友人,喜欢热闹。他弟弟曾则说他:“兄之天性忠爱悱恻,又喜交游谈䜩之乐,沉酣日夜而不厌。所至之处,宾客满座,皆引以为相契,而无逆虞傲物之心。”陈曾则记录其兄的文字有不少,谈性格谈做官谈为人等等,皆可见陈曾寿不仅性格温儒谦和,朋友们都喜欢他,对钱财他也不太看重。
陈曾寿在沪杭的朋友圈,档次甚高。冯煦、朱孝藏、陈三立、沈曾植、郑孝胥、朱祖谋、况周颐……这里面有曾经的地方巡抚、布政使,有过去的礼部侍郎,也有词坛宗主、大家,至于陈三立,虽然没做高官,但在青年时代就名满天下。他们的共性大体有二,一是不接受刚刚到来的新世代,爱以前朝遗老自居。再是皆为大文化人。
此时的陈曾寿,人虽不在官场,但因为唱和交游者中不乏闻人,且还偶尔代人写奏折,紫禁城的消息他会不时知道一点,因而很上心,很是牵记千里之外那个有名无实的皇帝。有关陈曾寿早期与末代皇帝溥仪的交集,因为没读过相关史料,不好妄猜,不过就他后来留下的文字看,君臣是能交心的。这大约也是他一直忠于没落皇室的原因之一。
有一段时间,也就是1925年之前,陈曾寿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绘画上。他作画速度快,不拖拉,与他写日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习惯不同,无论尺幅大小,今天画今日毕。这些画作,小部分用于馈赠,大部分后来被他出售以补贴家用。画作中扇面尤多,也不乏大画。陈曾寿的画价中上,扇面三至二十元居多,佛像观音像略贵,大画润格可至百元。这个爱好保持了一辈子,在生活艰难时刻,有一技傍身,可勉强度日。
其弟曾则记述这个哥哥对弟兄们甚好:“于兄弟子侄亲戚,则友慈之意,老而弥笃”。兄弟怡怡,可以想见。
1924年,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,暂居天津租界。一团人趋之若鹜,溥仪也曾招陈曾寿为顾问,陈辞而不就,不过曾赴津门见过溥仪。其后的六七年里,其母病逝,加上杭州生活费用较贵,陈曾寿又回到了上海,以卖字画、教书为业,一直到1930年,经陈宝琛推荐,陈曾寿担任了溥仪妻子婉容的教师,也就把家搬到了天津。就日记内容来看,他与婉容相处得不错,婉容也很尊敬这位老师,在听讲之余,不时给予一点日常的赏赐。
倘若溥仪旅居租界,直到临了,那倒也罢了,甚至能造就一个废帝与一群遗老遗少君臣相得的佳话也未可知。问题是,玖壹八来了。
按照后来溥仪自己的交代,他对被废被赶是有意见的,也做梦有一天能再坐龙椅。因此,日本人计划扶植他窜逃东北的时候,尤其是郑孝胥、罗振玉等人在背后撺掇久了,溥仪难免飘飘然。
忠于皇室甘做遗老,与夷族勾连谋一己之私,这两者是存在巨大分别的。去东北,陈宝琛不同意,陈曾寿也不同意。但他们都没经得住溥仪的挽留。这两位,一个是皇帝老师,一个是皇后老师。按照溥仪自述,陈宝琛的教育对他影响巨大。而二陈在事变之时,基本把溥仪的后路给看清楚了,那就是和日本人鬼混,不可能有好下场。但溥仪依然醉心于日本人给他编造的一个幻梦中。
陈宝琛屡谏无果,最后走了。
陈曾寿留下来了,做了一个小官。满洲国小朝廷建立之后,权力再分配,陈曾寿做的是“内廷局局长”。这个小官主管祭祀、陵庙、医官、女官、皇家私产等等。此后十年(1932-1942),陈曾寿和他时多时少的家人,一起居住在长春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提到二陈的次数不少,但他的一个判断,在事后看依然是误会了陈曾寿:陈曾寿对我大谈“建国之道,内治莫先于纪纲,外交莫重于主权”。所谓纪纲“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”,主权最要者是zheng令必出自我,总之一句话,我必须有权能用人,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。
幸好,陈曾寿留下了断断续续但总量不算少的日记,幸好陈曾寿的弟弟和女婿,也在这一段时间里为溥仪这个傀儡小朝廷服务留下了很多记录,都能证明陈曾寿也就是一个相对愚忠的文人,既无经天纬地的才干,也无操弄权柄的野心。
在东北十年,陈曾寿的日常主要是:绘画、写诗、下围棋、打麻将、与熟悉的三五好友应酬,以及很少量的所谓正经工作,比如在做祭祀活动的时候彩排、查看皇室私产、管管陵庙。在后期,他彻底辞职时,溥仪依然没让他走,而让他做了皇室教习,负责教育住在一起的亲贵的子弟读书。陈曾寿的棋力尚可,吴清源1930年代访问康德皇帝的时候,两人有过对局,陈曾寿负七子。
他的爱好还有:欣赏和摆弄菊花。他的经济来源除了薪资,还有绘画润格,并接受画作预约、写墓志铭,价钱均不低。以及偶尔的来自皇帝的金钱赏赐。而他的支出则是相当庞杂,除了养活一大家子人,还要不时汇钱给老家。但他并不善于理财,更不会钻营,因此即便混在傀儡皇帝身边,依然经常捉襟见肘,有一次回天津连路费都困窘,问皇帝预支薪水贰佰元,溥仪给了他三百。
就日记内容看,陈曾寿算溥仪的近臣,却不被倚重,有限的几次记录比较详细的对话,一般都是问文坛上的事,最近二十年,诗写得最好的是那几个啊?谁谁是什么家数啊?文章数谁最好啊?有空帮我整理和甄别一下紫禁城带出来的古画古书等等。偶尔,溥仪叫他做个命题作文,他也干得乐颠颠的,认真而不负圣恩。
陈曾寿自己觉得很是荣幸。这是很多做臣子的正常心态——总觉得自己很重要。
有一个好习惯,陈曾寿保持得不错,即不参与朋友或政客朋友之争。陈宝琛与郑孝胥不对付,陈曾寿几乎没帮腔。十多年日记里也就一两句腹诽,只不过在给溥仪的奏折里,陈曾寿常常痛心疾首,对郑孝胥罗振玉等人的野心直言不讳。他在诗坛名气不低,因此往来唱和者众,与散原老人、朱孝藏、陈宝琛、溥心畬等晚清大家都是交情极深。居京期间,溥心畬不仅送文房四宝,还直接送钱来周济。这林林总总都说明陈曾寿的为人温厚宽容讲礼。这在日记里也处处体现,对父母长辈出言必恭,对溥仪言必称上。
每年苏东坡生日,陈曾寿必召人雅集,诗酒唱和一番。
这些都说明他就是一个末世文人,有强烈的忠君思想,在变乱中他没太吃亏,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他不写宏大的句子,不说惊人的语言,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。他的大多诗作,哀而不伤,虽自云学黄山谷学李义山,其晚年诗风,恰如王老师所说,更像陶渊明。有人壮怀激烈以死报国,他做不出来;太过苟且巧取豪夺的事,他也不干。更愿耽于写诗绘画,小小的宴饮即可令其满足,师友的盛赞胜过末世D王的嘉许。
一个不错的文人,不幸生在变乱的时代,赶上了历史,半推半就亲历了历史,仅此而已。1911年之后,中国经历了很多个时期,皇帝没了、军阀混战、抗战八年……陈曾寿却只有一个时代,护着自己心目中的皇帝,奔走前后,诗酒生涯。他一直活在君君臣臣的古代,不愿意醒来。
两大册《苍虬阁日记》读完,留个印记。
公众号:私人趣读